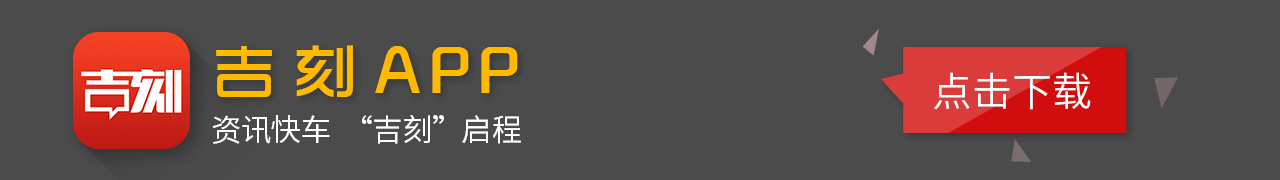□邴正
前几日,台湾作家龙应台一句“大河就是大河,稻浪就是稻浪”,引来了网上热议。我认为,龙应台的这句话触动了许多国人心中最深藏,世间最深沉的情愫,那就是对家乡的眷恋。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。我家就在岸上住,听惯了艄公的号子,看惯了船上的白帆。”乔羽、刘炽联袂创作了《我的祖国》,从我的童年,传唱了一代又一代。在我心中,大河不仅仅是大河,稻浪也不仅仅是稻浪,那是自己的家国深情。我也喜欢张寒晖那首《松花江上》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,那里有森林煤矿,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”每当我唱起这首歌,就情不自禁想起我那遥远的家乡,松花江畔的村庄。
我出生在长春市,但我父母的家乡就在松花江畔,一个叫积德增的小村庄。童年的时候,母亲常常给我讲关于故乡的故事,积德增位于松辽平原松花江畔,南临柳条边,东濒松花江。村名起源于我的家族开办的商号。我的祖籍远在山东(又一个遥远的家乡),明洪武二十五年(1392年),远祖邴三公从山东莱阳黄谷庄超巢村(今山东莱西市牛溪埠镇早朝村),迁至山东省德州恩县辛庄(今山东武城县李家户镇)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,我的十一世祖邴之钿、邴之鈖兄弟闯关东,先到吉林省九台县其塔木乡干沟子村落户,传至九世祖邴日有时逢清政府放荒,带全家迁至柳条边外开荒谋生。传至我的高祖邴芳林、邴芝林兄弟,家族渐富,农商并举,开设了名为积德增的商号(其实应为杂货铺,如今应叫乡村超市)。家族人丁兴旺,二人共生八子,十六孙,即我的八个曾祖,十六个爷爷。因未分家,共同居住,人口近百,遂因其商号而得村名“积德增”。
我的父亲很少讲家族故乡的往事。我的家族是一个大地主家庭,仅我爷爷兄弟两人名下的土地就有1500公顷,那另十四个爷爷名下有多少土地,母亲说不清。如平均计算,估计超过万公顷。父亲青年时代投身革命,又深受地主家庭所累,文革时候受批斗,罪名之一即“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”。估计这就是他很少谈及故乡往事的原因。
母亲的家族亦是清朝末年自山东登州府蓬莱县迁来,先祖王生生下十一个儿子,组成了一个略有薄田,靠租种我们邴家土地维持生活的中农家庭。他居住的小村子如今就叫王生屯。我的十一个姥爷个个是好庄稼把式,日子还算过得去。这些姥爷有的善种田,有的善养马,有的善狩猎,有的善捕鱼。那时的松花江畔,湖泊相连,湿地纵横。童年的母亲,常和姐妹们去泡子边采鸡头米,拣野鸟蛋。每至夏日汛期,松花江泛滥,泡子里水漫金山,江湖一片茫茫,如似海洋,连田里垅沟中都可捉鱼摸虾。冬日来临,江湖冰封,田野皆白,勤快的姥爷们扛上土枪洋炮,带上自制钩、夹笼套索,常能捕捉到山鸡野兔。某年冬天,母亲去她的姥姥家过年,那个村庄临近柳条边的山岗。刚刚把年夜饺子下锅,一家人在火炕上唠嗑。一只动物闯进柴门,在灶间喘着粗气,“啪嗒啪嗒”地来回折腾,把灶间弄得翻天覆地。一家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,紧闭房门,一直到那动物折腾够了,扬长而去。根据在雪地上留下的巨大脚印推断,应该是一只黑瞎子(狗熊)。而那一锅年夜饺子,都煮成了片儿汤!
其实大概两三岁时,母亲曾背着我回过老家。只依稀记得路过一个叫“温家泡”的湖泊。十一岁那年春天,父亲终于从不许回家的“学习班”(大概就是所谓的“牛棚”)回家了,还有几天假期。父亲被批斗间患了严重的肝炎,有人推荐偏方,吃苏子油烹饪的食品可治肝炎。于是,父亲领着我回老家去买苏子油。我随父亲乘火车至德惠,转乘长途汽车至朝阳公社,在乡间土道上行走了几里路,来到舅舅家。舅舅家距离我的老家还有几里路程。也许父亲还有顾虑,并没有带我回去。积德增村此时已改名叫双城子大队,因附近有辽金时代古城而得名。此城因有内外双重城墙而被称为双城子。
第二天吃完早饭,我的几个表弟表妹带着我去看松花江。
呵,这就是多少人反复吟唱的那条大江吗?那清澈的江水,仿佛从天边浩荡簇拥而来,又义无反顾地奔涌着向西北方那广袤的原野流淌而去。水面的波浪辉映着朝阳,泛起点点金光。水边的野草丛柳,伫立在激流之中。仿佛逐水而倒退迤行,更显江水的激流猛进。江水在我身边低声地吟唱着、欢哗着、涌动着、奔流着。多年以后当我阅读罗曼·罗兰的名著《欣悦的灵魂》时,那种隐藏在内心的冲动,时而如春潮涌动,时而如潜流舒缓,时而如倏忽迸发的自由不羁的情愫,不正如松花江水一样!她不知疲倦,永不止歇,不因融融春水的温情脉脉而止步,不因千里冰封的表面平静而停歇,不因狂风暴雨的鼓噪而成脱缰的野马,不因炎炎烈日的蒸烤而成奄奄一息的细流。千百年来,松花江一如既往,从亘古洪荒到沉舟侧畔,她就这样奔流,奔流!祖先冒死的闯荡与垦荒,到母亲那苦难与动乱的青春,直到少年的我,伫立在她身边,仿佛从她的激流中看到逝去的五千年古老历史,看到历代先人跋涉的足迹,看到自己从哪里来,又到哪里去!松花江的确就是一条大河,是一条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东北人的母亲河!
我们在江边奔跑,跳跃。跑着跑着,在江边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石碑,静静地倒卧在江边,那是一座汉白玉雕刻的石碑,碑首、碑身、碑座分离,碑上刻有“嗣因边里人烟稠密,水域鱼稀,前于乾隆二十六年,经本省将军奏明,由边外起,南至松花江上掌,下至红石砬子、石子滩等止,其间沿江均为捕贡、晾网之区……严禁私捕,侵占地址,为此办理,百有余年。敬谨奉行……”。表弟告诉我,这是一座古碑,文革时红卫兵将古碑推倒。后来我才知道,此碑名曰“贡江碑”,为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所立。古城、古碑、大江、大平原,把古老而壮阔的传统和情愫深深埋藏在一个少年的心底!
1995年5月,我作为策划与顾问,随大型电视纪录片《松花江日记》剧组爬上长白山天池,从冰封雪盖的松花江源头开始,沿1927公里长的松花江行进,直到松花江汇入黑龙江的汇合口。在天池水畔,我们经历了长白山主峰上的狂风暴雪,看着松花江之水怎样从天上来。在二道白河边,我们考察宝马古城,捡拾辨认过金代祭坛残留的瓦砾。在两江口附近的大兴川,我们寻访过整村的山东移民。在松江河阴的夹皮沟,我们踏查拜祭过抗联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将军埋骨的密营遗址。在桦树林子,我们追踪过东北著名金矿矿主、啸据一方的韩边外的往事。在阿什哈达摩崖,我们辨认过大明辽东都司都指挥使刘清刻下的豪言壮语。在郭尔罗斯草原上,我们观看了满族新城戏《铁血女真》,被蒙古族女歌手达古拉灌得酩酊大醉。在松花江上的老苗家小通的小岛上,我们冒雨围坐在渔窝棚里,品尝江水炖江鱼。当我在同江口,终于面对青色的黑龙江与银色的松花江两条巨龙融汇到一起,合流成浩渺水天时,我隐约记起当年第一次面对松花江时的情景。松花江啊,松花江,这些年来,你一直在我心中流淌!我终于沿着你开拓出的水路,蹚着你的身躯,追随你走下雪山,走下悬崖,走出森林,走出山岭,走过田野,走过荒原,走过城市,走过乡村,终于走到更大更宽的水面天际……
一条大河,就是大河。可对河边生长的人们来说,那是家园的河,那是亲人的河,那是故乡的河,那是心中的河。心中的河,会永远永远在人们的心中流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