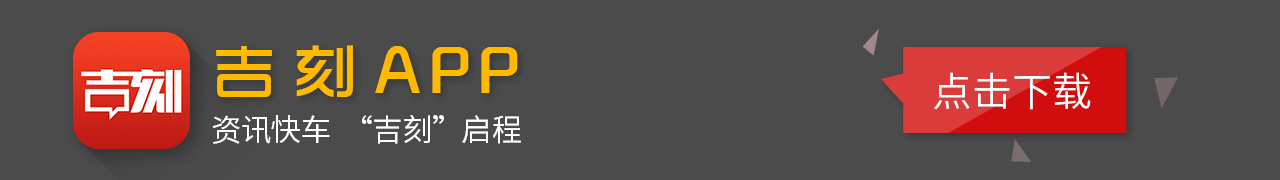□李咏瑾
丁酉鸡年。如今的城镇乡村,大概很少能听到寒冷年节下雄鸡的啼鸣了,可是最认乡土情的国人,人人本质上都是候鸟,一到每年的这个时刻,仿佛都有个声音在内心之中殷殷提醒:天寒地冻,家人在等,胡不归?
那一刹那,万般功名利禄潮水一般“哗”然褪却,中间孤零零的你穿着母亲当年添置的旧袄,才觉得自己实在是坚强得太久,手脚冰凉,现在一心一意只惦记家乡的热锅暖灶。而一遍又一遍刷不到火车票的满脸焦灼,才是你最真实的本相。
当“动车”还是一个存在于报纸上的遥远概念时,我过年回家,是坐一种叫做“快车”的绿皮火车。那时刚刚毕业,到年底足足攒了一万块钱,板砖那么厚一叠,还束着银行的封条,塞在羽绒衣的内袋里,雄赳赳气昂昂登上火车,每隔5秒钟拍拍胸口,顿生好汉一条的豪迈气概。
不料那天火车可能是出于警醒旅客的需要,小屏幕上来来去去放着一部叫做《天下无贼》的旧片。我就看着王宝强扮演的小民工在归乡的火车上遭人耍弄,一包血汗钱在不同人等手中周而复始、来来回回——看起来是一列火车,其实这短短而又纷繁的旅途,何曾不像我们颠沛流离的人生?只有我自己知道,当我最终把那捂热的一万块钱放到母亲手中,然后埋头狼吞虎咽着桌上的饺子时,内心是无比安宁的。以前在父母庇护下,我的世界是如此的小而温暖,只有我的家这么100平方米大,这一万块钱,是我跌跌撞撞从慌乱的外部世界里衔回来的第一枚果实。
而在更早更远之前,年节下我们要回的家还不是父母所在的那个家,血脉指向了更远更深的偏僻小城里那个外公外婆的家。长江磅礴的水系分如细丝,精微地渗入到这里广袤的大地上,外婆外公的家就在龙须河边,前面的桃花山随着河势蜿蜒,起伏的河浪催生着初春桃花即将到来的灿烂。
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一路挤上长途大巴车,车里旋即挤上更多的人,把过道和司机旁边的引擎盖都挤得满满当当的。相连的两个位置上挤坐着我们一家三口,尽管脚下全是行李包,已经是整辆车上非常好的运气了。我被紧紧地裹挟在父亲和母亲之间,在熟悉的体温中醒来又睡去,朦朦胧胧在车厢密闭而浑浊的气味中,忽然嗅到了一阵甜美的气息。那是母亲怀里抱着的醪糟罐子在轻轻晃荡,罐子口的蓝花包袱皮上已经微微浸湿了一小块。
那时年轻的父母并不富裕,在探望他们的父母时,他们觉得献上一罐才酿好的甜醪糟,唤出自己生养的孩子,给姥姥、姥爷恭恭敬敬地磕个头、问声好,这种血脉的延续与归宗已是最大诚意的礼物了。联想到现在都市里的男女大龄未婚,还有很多人选择了独身主义和丁克家庭,固然是人性的解放,以及个体的属性渴望得到尊重,但从另一方面来说,未尝不是对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先祖欠缺了一份重要的礼数。
而在更早远以前,我回归的家庭不是父母的家,甚至也不是祖父母的家,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?那时我才两三岁,跟着从事野外勘探工作的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环境恶劣,运送勘探设备上山的时候没有现在的专用车辆,往往是靠人力用扁担挑,一边的箩筐里是孩子和棉被,而另一边的箩筐里往往是发电机或测量仪——这导致我在箩筐里的旅途总是弥漫着机油味。而每逢过年到了下山的时候——哪怕直到现在,我国的地勘工作人员们往往也要奋战到大年二十九——在那时的大年二十九,我仍旧坐在箩筐里,头上覆着一条旧被子被挑下山去,所不同的是另一边的箩筐填满了向山上乡民收购来的稻米、腊肉和鸡蛋等年货。
一年过去,在艰苦的环境中,孩子又养大了一岁,一部分年终奖金换来的稻米、腊肉和鸡蛋,让年轻的父母喜悦地感受到自己成长得越来越独立而坚强。夜幕渐黑,终于回到了山下的驻地,那是一排排勘探队员的活动板房,属于我们的是其中一小间,四面漏风。“就是这里了。”父母满意地进屋,踩了踩地面,看了看四周。“家”字就是上面有个庇护的屋顶,下面有着绵延不绝繁衍而来的“豕”(小猪),此时此刻,我从箩筐里的毯子下露出了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。